展板2-1
反共刺青
一九五〇年年初,共軍集結兵力,預計渡海攻臺。但同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立刻派遣第七艦隊巡航臺灣海峽,於是毛澤東選擇先鞏固北方局勢,放棄攻臺計畫。
韓戰停戰之後,中共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共有兩萬兩千多人遭到美軍俘虜,美軍讓戰俘自行選擇要返回「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俘營裡面,國民黨幹部滲透其中,鼓勵戰俘們回歸「回歸自由中國」,並且為了加強戰俘們選擇遣返臺灣的意志,協助戰俘們刺下「反共抗俄」或「殺朱拔毛」等刺青。後來共有一萬四千名志願軍戰俘選擇遣返臺灣,中華民國當局也以「一二三自由日」等歡迎活動,大肆宣傳「反共義士」來歸。
國共對立的時代氛圍,在這群軍人的皮膚上,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也象徵國家強制將意識型態銘刻在人民身上,而一旦被烙印就失去選擇自由;或者選擇了錯誤的陣營,就要面臨被鬥爭的下場。
一九八七年之後,兩岸開放探親,許多老兵必須先抹除身上的印記,才有辦法返鄉探親。張曉風寫〈一千兩百三十點〉,講述老兵拿到退輔會補助,在身上用雷射點了1230個點,把刺青消除,連同把過去的政治信仰也去掉,只剩蒼白衰老的肉體。
展板2-2
什麼都沒了,他忽然明白。「殺朱拔毛」沒了,「反共抗俄」沒了,地圖沒了,國旗沒了,不成功便成仁也沒了……從今以後什麼都毀了跡,彷彿戴了四十年的戒指一旦除下,變只剩這指頭上一圈白痕。空空洞洞的白。一無所有的白。
張曉風〈一千兩百三十點〉(1996)
這個長鏡頭之前,有一個看似隨意的取鏡,主景是一個中年人,吸著像是插在竹管還是濾嘴上頭的菸,百無聊賴地站在摩托車旁邊。由於鏡頭是側著拍的,因此沒有拍到他的右手是從小臂齊根斷去的。沒有斷的那隻手臂上有青天白日旗的刺青,那個人就是老李。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2011)
 龐大的醫療費除去臂上胸前
龐大的醫療費除去臂上胸前
背上的圖騰
鄉關一節一節地打通
把一生的漂泊暫寄籬外
拎著見得人的大包小包上路
與眾親友
哭過 笑過
醉過 醒過
唏噓過 扼腕過
血脈賁張過
有所思過
最終歇在睡與醒裡
下半夜
頻頻小解
驚見圖騰一一復活
啃嚙一截枯木上的綠苔
馬驄〈刺青〉(2006)
.jpg)
展品04〈圖騰啃嚙枯木上的綠苔——試析馬驄教授的短詩《刺青》〉手稿
作家一信評論馬驄〈刺青〉的手稿,解析馬驄詩裡的意象。圖騰象徵刺青背後的政治壓迫,不斷啃嚙著一如枯木的老兵,以及老兵身上的綠苔(刺青及老兵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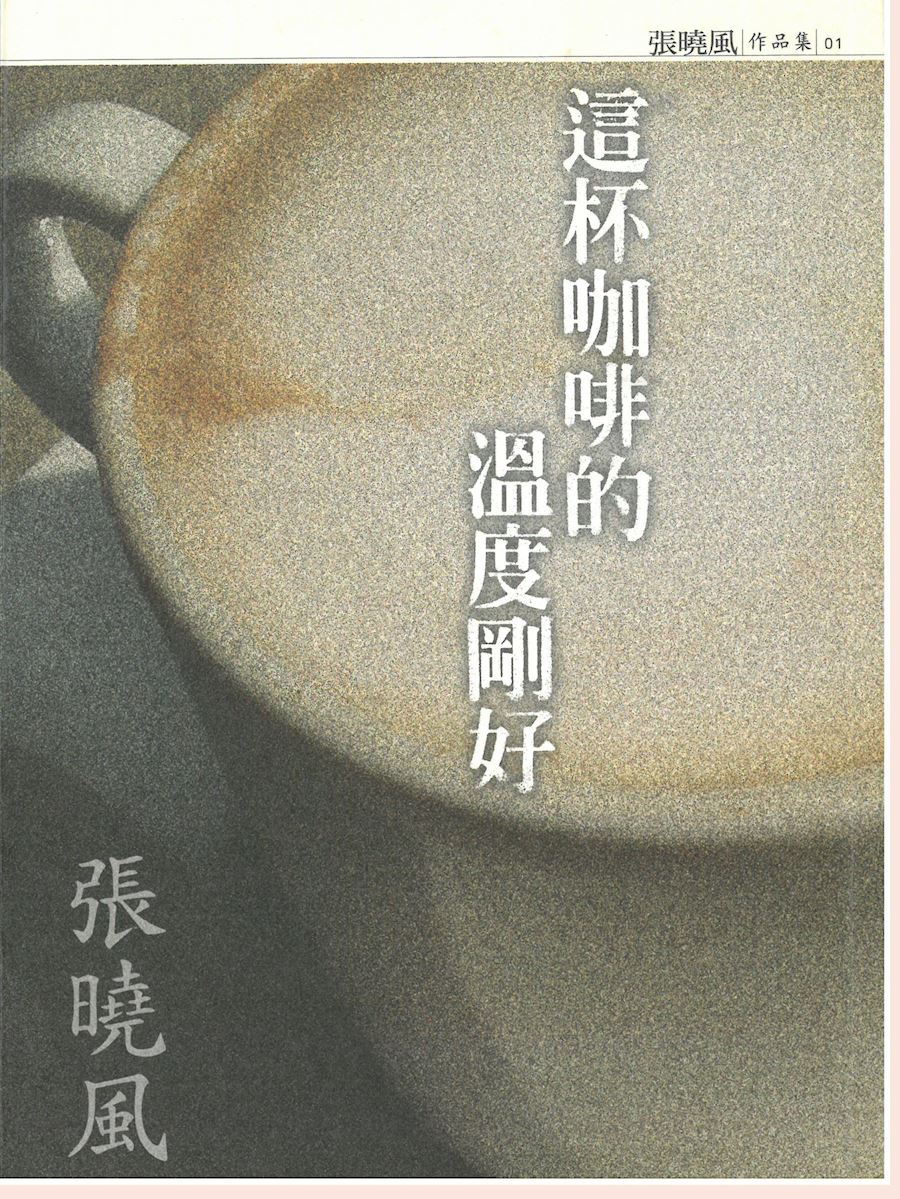 書籍9
書籍9
.jpg) 書籍10
書籍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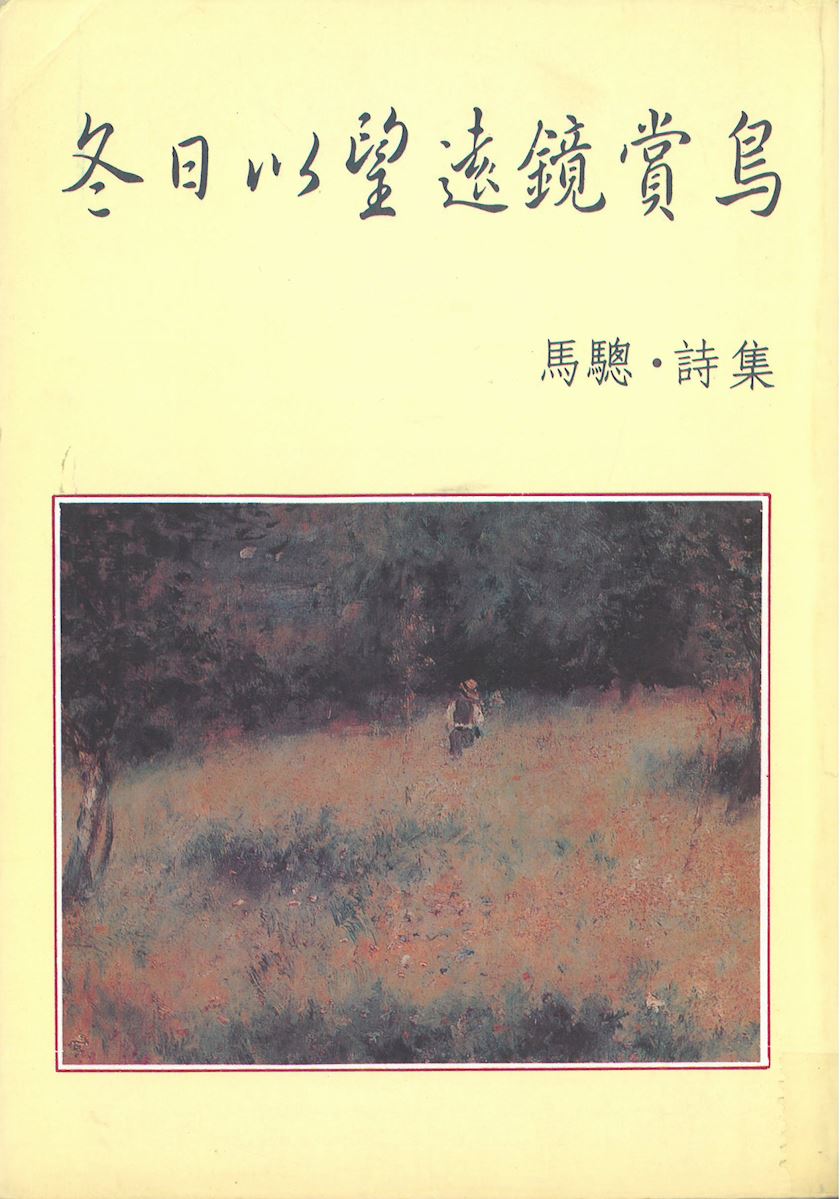 書籍11
書籍11
展板2-3
我在我不在的地方
 在臺灣島內,蔣介石透過宣傳「自由中國」以及想像的中華民族法統,維繫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包括日語、臺灣台語、臺灣客語及臺灣原住民各族語言的管制禁絕,原住民族的改漢人姓氏,乃至「籍貫欄」等政策,都是強化了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的認同。
在臺灣島內,蔣介石透過宣傳「自由中國」以及想像的中華民族法統,維繫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包括日語、臺灣台語、臺灣客語及臺灣原住民各族語言的管制禁絕,原住民族的改漢人姓氏,乃至「籍貫欄」等政策,都是強化了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的認同。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即是早在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將所有日本遺留的符號都抹去,包括路名、地名跟大大小小的神社與銅像等等。接著仿照上海,將中國地圖烙印在臺北市街頭——北至吉林路、南至廣州街——身在臺灣,就可以想像整個神州大陸。
雖然戰後移民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返回家鄉,但透過符號的改造與再創造,凍結了時空,將鄉愁移植到這座原本素昧平生的島嶼。
一九九二年戶籍法還沒修正以前,臺灣人身份證上登記的籍貫欄,都是以父親出生地為主,也就是說,雖然戰後移民的後代出生在臺灣,但籍貫仍然要填寫中國的省,對於許多從未到過中國大陸的戰後移民後代來說,籍貫欄上的地名是陌生的,卻是一種對於遙遠鄉愁的連結。
籍貫作為族群劃分,曾經影響臺灣島內的階級晉升。國家晉用公務員的兩大考試:高考及普考,是依照省籍劃分,並照該省人口定額錄取。例如一九九一年高普考「全國」定額是599人,臺灣省佔21人,江蘇省佔44人,蒙古地方則佔8人。雖然臺灣省政府有另外開辦臺灣省籍的高普考,而且在一九六二年之後,高普考採臺灣省籍加倍錄取政策,比例嚴重失衡的問題有所改善,但加上甲乙丙丁四種特種考試後,就人口比例上,戰後移民(外省籍)還是佔有絕對的優勢。
展板2-4
許多年後我曾遇見一位學弟,瘦削的臉留著一小撮山羊鬍子,我記得他在閒聊中苦笑地告訴我:他從小學到大學,各種身份資料的籍貫欄皆是填寫著「察哈爾」。他說:「我是察哈爾人」他是到很後來才知道;現在的中國行政區裡,已經沒有「察哈爾」這個地方了。我充滿興趣地問他:那你父親當初為什麼會輾轉跑來台灣?從那麼大老遠的地方。我記得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凡有籍貫欄填寫著一些怪地名的傢伙,你若私下和他熟稔起來,他們絕對有一海票稀奇古怪的關於他們父親當初逃難的故事。什麼全軍團的人被共軍圍堵在四平街上,活活餓死了四、五十萬人,只有他父親,因為每次部隊開伙吃剩的包穀梗子,他都捨不得,把它們埋藏在一處地方。於是到了全部的人被戰術圍堵到一個個餓死倒下,他父親即是靠挖出的幾十枝包穀梗子,嚼得牙肉賁血,卻保下命來。
駱以軍《月球姓氏》(2000)
展板2-5
我厭煩不精確的事物,像這麼一個變形走樣的中國之所以仍然壓在我的玻璃墊下,或許只因為它成為一種道德警惕。六、七〇年代,我也曾在一些中小學校舍的牆壁上看過中國全圖的浮雕,台灣的比例被誇張的放大許多,厚實地蜷伏在大陸的東南隅,上面站著忒大一座燈塔,光照寰宇,東北向的每一根光芒都刺穿塗刷成紅色的大陸。
林燿德《迷宮零件》〈地球零件・地圖〉(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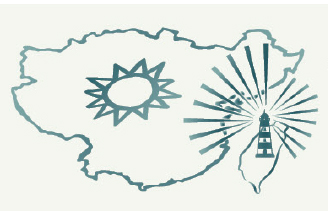 「我不是台灣出生的嗎?為什麼叫贛生?!」讓人叫這麼多年,現在才發現這名字起得不對。今天豁出去了,非得跟父親弄清楚不可。「你媽媽是在老家懷你的,到此地不到兩個月就生產了,當然叫贛生,這是不忘本的意思。」他不服氣,乾脆再豁出去一次,把國語的「贛」和台灣話的「幹」同音以及後者豐富的含義很費力很曲折很小心又很不清不楚地跟父親說了個不明不白,讓他知道自己讓他害得有多慘。「不要理他們!此地的孩子,就是沒出息!」就你有出息,收垃圾!他只敢在心裡頂。
「我不是台灣出生的嗎?為什麼叫贛生?!」讓人叫這麼多年,現在才發現這名字起得不對。今天豁出去了,非得跟父親弄清楚不可。「你媽媽是在老家懷你的,到此地不到兩個月就生產了,當然叫贛生,這是不忘本的意思。」他不服氣,乾脆再豁出去一次,把國語的「贛」和台灣話的「幹」同音以及後者豐富的含義很費力很曲折很小心又很不清不楚地跟父親說了個不明不白,讓他知道自己讓他害得有多慘。「不要理他們!此地的孩子,就是沒出息!」就你有出息,收垃圾!他只敢在心裡頂。
遠人〈異鄉人〉(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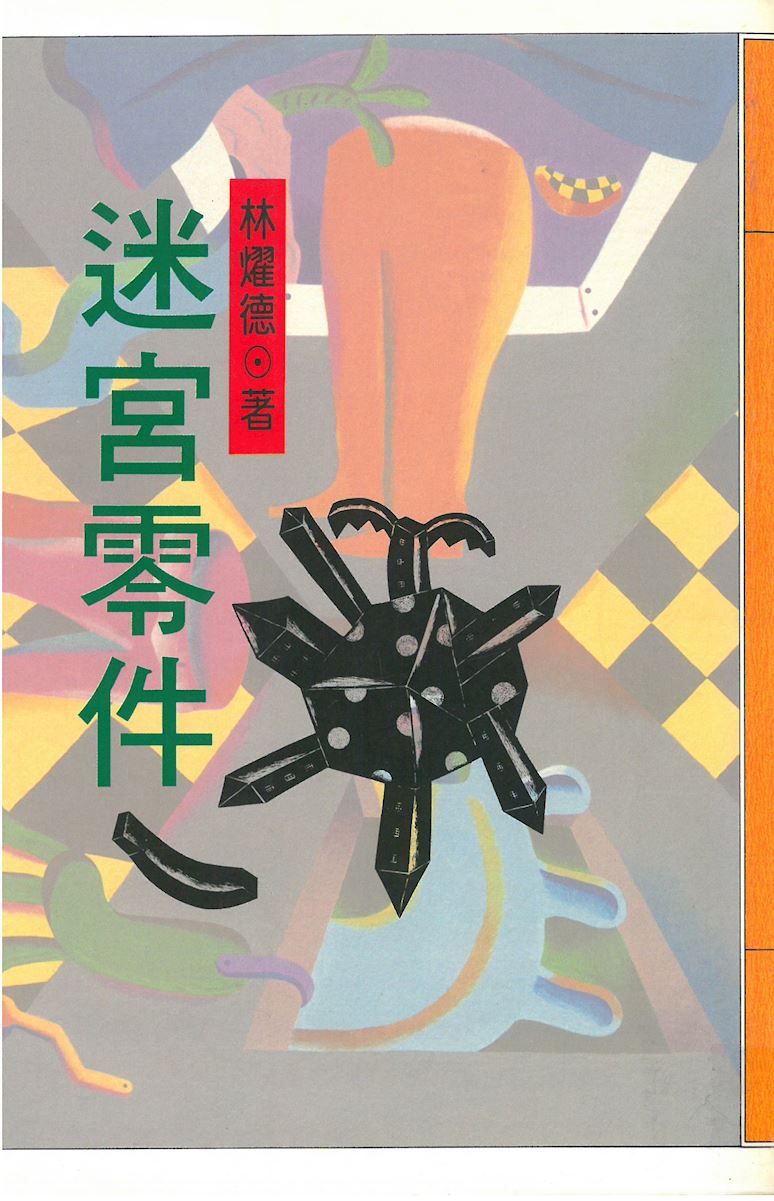 書籍12
書籍12
 書籍13
書籍13
展板2-6
尹雪艷們與王雄們
 雖然我們都統稱一九四五年後來臺的中國移民叫做「外省人」,但實際上,這群人內部有著非常巨大的差異。許多戰後移民有些可能是在中國大陸被抓去當軍伕、也可能是流亡學生,也可能是像軍人作家桑品載一樣,十歲就孤身流亡到臺灣的。
雖然我們都統稱一九四五年後來臺的中國移民叫做「外省人」,但實際上,這群人內部有著非常巨大的差異。許多戰後移民有些可能是在中國大陸被抓去當軍伕、也可能是流亡學生,也可能是像軍人作家桑品載一樣,十歲就孤身流亡到臺灣的。
光就「榮民」而言,軍中階級差異及退伍時機就有天壤之別——一九五二年,韓戰進入尾聲,政府公布〈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軍官在28歲以下,以及普通士官及士兵不得結婚。同時推行精兵政策,強制老弱軍人退役,並強制延長年輕力壯及具有戰爭經驗的士官的退役時限。
在一九六一年訂立〈陸海空軍軍官及士官服役條例〉以前,約有八萬多名基層士官兵退役,這群被迫、或者因為不堪軍中限制而退役的榮民,僅領到微薄的退休俸:三個月薪俸,主副食費約四、五百元,另外加上蚊帳一頂、草蓆一件及衣服兩件。
這群龐大的底層榮民,沒有親人可依、沒有眷舍可住,更沒有任何終身俸及醫療保障;而他們孤身一人,面對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甚大的臺灣社會。若是沒有一技之長,或者找到穩定工作,就很容易淪落為真正的底層貧民。
展板2-7
尹雪豔總也不老。十幾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樂門舞廳替她捧場的五陵年少,有些頭上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有些來臺灣降成了鐵廠、水泥廠、人造纖維廠的閒顧問,但也有少數卻升成了銀行的董事長、機關裏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麼變遷,尹雪豔永遠是尹雪豔,在臺北仍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一逕那麼淺淺的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下。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1971)
我和王雄也漸漸混熟了,偶爾他也和我聊起他的身世來。他告訴我說,他原是湖南鄉下種田的,打日本人抽壯丁給抽了出來。他說他那時才十八歲,有一天挑了兩擔穀子上城去賣,一出村子,便讓人截走了。
「我以為過幾天仍舊回去的呢,」他笑了一笑說道,「哪曉得出來一混便是這麼些年,總也沒能回過家。」
白先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1971)
展板2-8
他的收入每月實際是進不抵出。他(毛毛)稔悉每月月初得薪時候的狀況:他爸爸何媽媽閉門在他倆的臥房裏,伴在一個墨烏漆皮小箱箱旁旁,分數著錢目。他的媽媽是時臉顏更病,脾性更燥,箕距在塌塌米上,兩條腿挺開。每一月到廿號左右,他的爸爸,由於錢已不夠划,遂得去處中處處借湊。
王文興《家變》(1973)
 「我說過我要做你老婆,」伊說,笑了一陣:「可惜我的身子已經不乾淨,不行了。」
「我說過我要做你老婆,」伊說,笑了一陣:「可惜我的身子已經不乾淨,不行了。」
「下一輩子罷!」他說:「此生此世,彷彿有一股力量把我們推向悲慘、羞恥和破敗……」
遠遠地響起了一片喧天的樂聲。他看了看錶,正是喪家出殯的時候。伊說:
「正對,下一輩子罷。那時我們都像嬰兒那麼乾淨。」
陳映真〈將軍族〉(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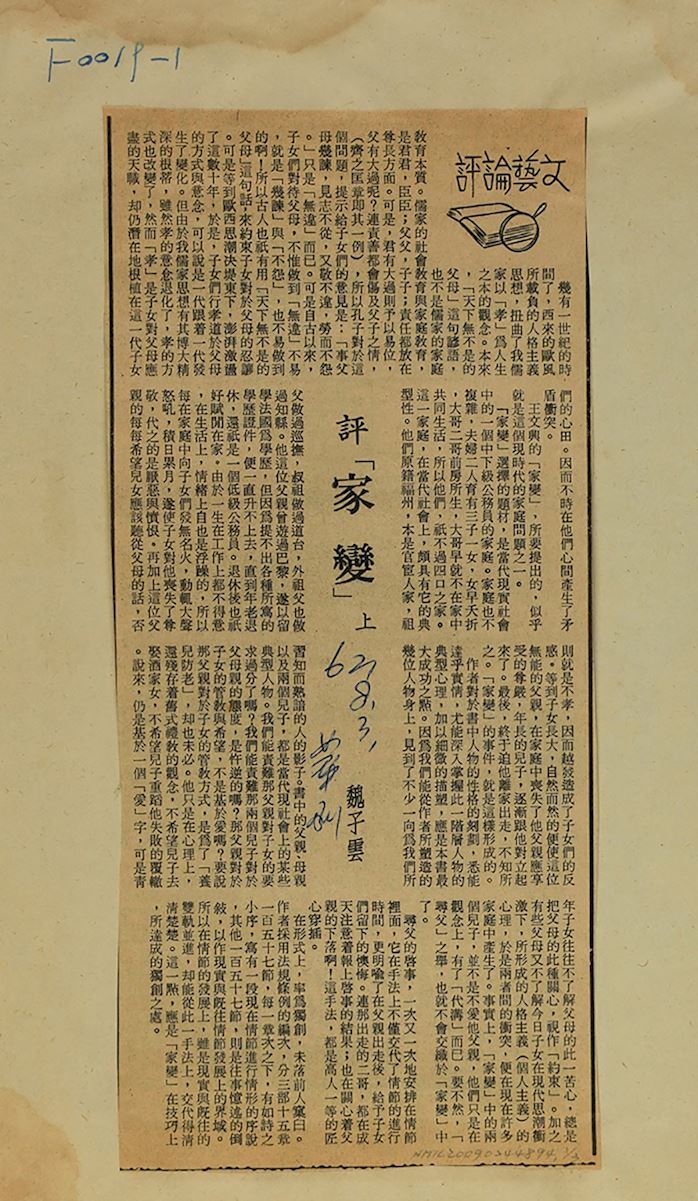
展品05「評家變(上中下)」剪報
魏子雲〈評《家變》〉於1973年刊登於《中華日報》。魏子雲分析王文興《家變》的形式,在文中最後批判了《家變》所呈現的家庭觀與社會觀與不合傳統的儒家道德。
 書籍14
書籍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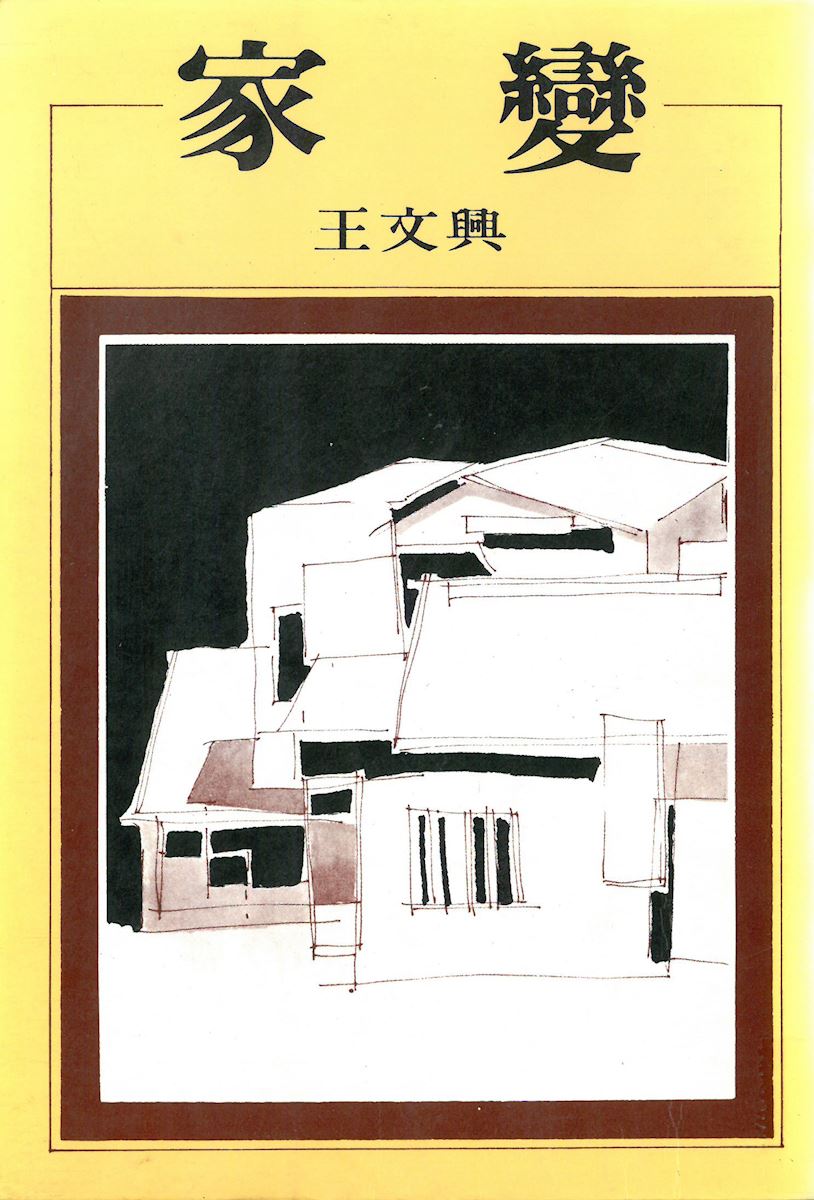 書籍15
書籍15









